王延巍:《瘟疫与人》:既是医学现象更是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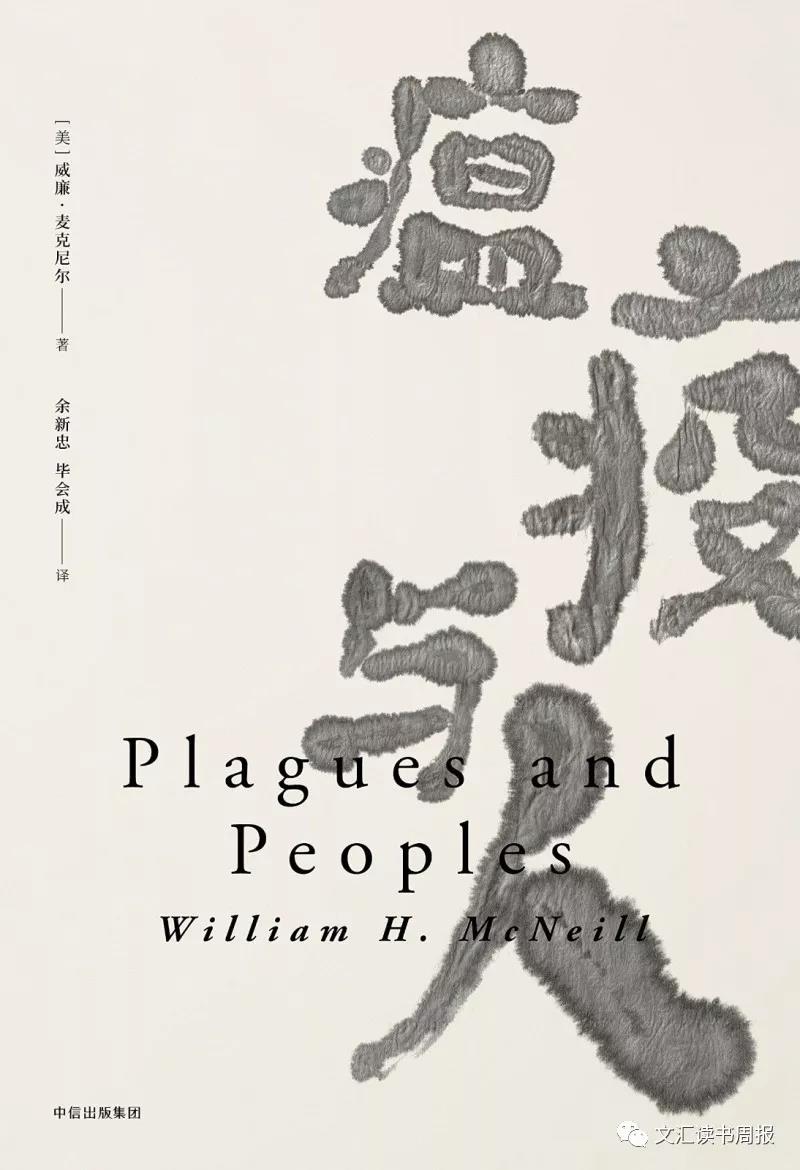
《瘟疫与人》 [美] 威廉 · 麦克尼尔著 余新忠、毕会成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瘟疫,令人毛骨悚然,象征着死亡、毁灭。瘟疫属于医学、生物学范畴,但绝非仅仅是科学领域事件,无论其前因还是后果,都深入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而由此角度切入并勾画出一幅大历史画卷,则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上世纪70年代,计算机尚未普及,互联网还无踪影,更无海量数据,史学大家麦克尼尔便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迄今为止依然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瘟疫与人》采取常见的时间线推进方式,从人类史前文明狩猎时代开始,直到近现代,演绎出瘟疫与人类社会的交融过程。作者并未平铺直叙,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和主要时间节点来阐述人类社会与瘟疫的相互影响。由此,欧亚疾病大交融、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跨越大洋的交流等,成为该书核心的章节主题。从这些标题也可看出,其核心就是瘟疫与人类的“交融”。
所谓瘟疫,可解释为致命性疾病的传播过程和结果。但并非每种知名的疾病都能造成瘟疫,即使其本身具有传染性。试想,如果人们以人数不多的群落散居于地球,老死不相往来,瘟疫还能成为令人谈之色变的现象?从某种程度说,瘟疫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的伴生现象。在人类狩猎和采集时代,能供养的群体人数有限,很难给瘟疫肆虐提供舞台。进入农业社会后,单位面积的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终于,更大的人类群落出现,随之,城市、国家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人类迈入文明社会。在密集的城市,更高频度的社群交际过程中,瘟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人类史的记录,死神开始挥舞镰刀,留下令人难忘的痛苦与噩梦。
在体现人类与瘟疫的互动方面,作者抓住重点,以瘟疫与人类“交融”为核心,即人类社会的重要变迁尤其是人口大范围流动的节点,以充分体现瘟疫既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人类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对美洲的殖民过程极具代表性。当时欧洲殖民者仅以少数人就征服了美洲,特别是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皮泽洛征服印加帝国,双方人数悬殊更是到了离谱的程度。作者认为,正是瘟疫在其中起了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虽说美洲帝国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无法与欧洲相比,但真正放大欧洲对美洲毁灭能力的,还是其带去的致命病毒。彼时,美洲帝国已进入城市化时代,相对密集的人口及其毫无免疫力的体质,为瘟疫肆虐提供了条件。由此,全球化过程既是不同文明交互的过程,也是瘟疫扩散并引发毁灭性冲击的过程。从表象看,这似乎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带血的注解甚至否定,然而,跨越高山大海是人的本能,全球化过程也是创新的机会,最终将提升人类整体福祉。对于这一过程中瘟疫的扩散和影响,作者的叙事脉络特别是最后一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将瘟疫的每次兴起与消散过程嵌入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深刻揭示了人类发展和交融过程中伴生的瘟疫,只能由进一步的发展和全球化协作来解决。
事实上,欧洲人携病毒扫荡美洲之前,欧洲大陆也经历了由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引发的人类大迁徙和瘟疫爆发周期的洗礼,“黑死病”至今令人闻之色变。瘟疫就这样形成一个渐次扩散,又逐步提高更多人对瘟疫免疫能力的过程。而伴随人类医学能力的提升,以及城市和社会治理经验的丰富,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力正在减弱。人们发现,尽管很多疾病的治疗仍充满难度,但控制瘟疫爆发仅需要简单而到位的清洁措施——干净的水、适当的隔离。伴随此过程的则是信息公开和顺畅传达,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该书完成后,人类再度经历了几次病毒的爆发,但其造成的伤亡和社会影响似已很难让人冠以“瘟疫”之名。在现代社会,人类交互更频繁,交通更便利,理论上讲病毒传播“效率”更高、扩散更快,瘟疫爆发的危险更大。“非典”爆发即为实证,它迅速在世界各地出现病例,扩散速度极快,致死致残率很高。但人们发现,与历史上的重大瘟疫相比,“非典”的破坏性已相对弱了很多。现代化背景下,病毒传播速度加快,同时也已形成更成熟的应对体系和方法,网络则更有利于全球化经验、资源的分享与协作,从而相对迅速地控制并遏制了“非典”的破坏性。2014年,在现代化程度与社会治理能力不高的西非,埃博拉病毒迅速蔓延,但凭藉当地政府的重视并依托其他国家成熟的经验和帮助,疫情很快得以控制。2017年、2018年埃博拉病情再度出现时,当地政府已具备充分经验,很快控制并扑灭了疫情。
瘟疫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冲击力总体上呈逐步衰减之势。人类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既让瘟疫得以肆虐,也让人类终于可以科学地对抗瘟疫。今天,人类不能说已可坦然面对任何未来的新疫情挑战,诸如“沙特超级病毒”的新闻依然令人恐惧,但或许正是这种恐惧和不安感,使人类时刻保持紧张感,从而让这些病毒最终未能成为瘟疫。当然,如“黑死病”一般摧枯拉朽的瘟疫已成遥远的记忆,如天花几乎毁掉北美原住民的历史几乎不再可能重演,但瘟疫与人类的互动仍在继续。希望这种互动更多地在瘟疫的科研和防治中继续,让更多人不必直面那曾经令人战栗的伤痛。
(来源:中国作家网)




